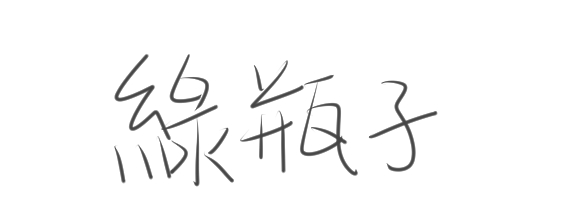我們一起吃了一頓好吃的晚餐,聊了聊這幾天發生的事情(雖然絕口不提吵架的那一晚),然後對著彼此微笑著。我們都在學習怎麼粉飾太平,學習怎麼避開傷口的位置,學習怎麼說服自己甚麼事情都未曾發生。
他牽著我的手,一起走進我家的那條巷子裡。車子停在巷口外的一個臨時車格裡,這條路上,只剩下我們彼此的腳步聲。
我輕睨他的側臉,雖然只有微弱的路燈照耀著,但是依舊可以清晰可見他的黑眼圈。
不知為何,我竟然為了他的憔悴而感到些許竊喜。
想到他或許也不想離開我,或許也為我的那席話而感到心傷,甚至夜裡輾轉難眠而染黑了眼眶,我的內心突然像是得到了一絲慰藉而歡喜不已。
我真是一個無可救藥的人啊。
「上來嗎?」到了樓下,我在鐵門前如此悄聲問道。
我看見他眼裡閃過一絲猶豫的神色,卻又很快的消失了。
「好。」他說。
我很驚訝他的乾脆,卻也沒辦法多說些甚麼。於是我跟他一起上了樓,然後我開了鐵門,到廚房替他裝了一杯水,最後坐到他面前的地板上。
他沒有褪下外套,像是一個第一次到訪的陌生訪客,坐姿如此客套,然後接過我的水杯,輕輕啜飲了一口。
我知道他有話要說。可是我並不想聽。
「凱璇,我想跟妳談談。」他的語氣放軟,是我最沒辦法抵抗的口吻。
「我不想談。」我像一隻受到驚嚇的刺蝟,馬上把自已縮成一團,然後用兩隻手掌把自己的雙耳給完全掩蓋住。
我不是不想談,是不想談我所不想談的話題。
你為什麼總是不懂呢?
「凱璇,妳不要這樣。」他的語氣像是在懇求,即使我遮住了耳朵,還是沒有辦法讓聲音不要竄入我的耳裡。
「我不要!」我任性的說著。
我聽見他嘆息的聲音。我知道他一定覺得很挫敗,他一定覺得我很煩,可是卻又沒辦法拿我怎麼樣。
我總是掐著他個性的這一點不放,因為我很了解他;而他總是在這種時刻裡放棄溝通,因為他也很了解我。
說到底,到底是誰比較卑鄙呢?
「凱璇。」
他這一回,沒有放棄。他伸手掀開了我遮住耳朵的手掌,我抬頭望向他,卻讀不出他臉上的心思。
「我們好好談一談,好嗎?」他像是在哄小孩一般問著我。
「……嗯。」我無可奈何,只好乖乖就範。
他把我的雙手拎起,然後放在他的腿上,輕輕的用他的手將我包覆住,我感覺到他溫熱的手溫,以及彼此脈搏的律動。
他很緊張,我也是。
「對不起,我沒有接妳的電話。」他說。
我盯著他看,喉頭卻說不出任何一個音,即便我只是想發出一個「嗯」回應他罷了。
「這幾天,我一直在思考我們之間的關係。」他平靜的說著,「然後想到一些以前我們經歷過的事情,還有那天爭吵的時候,我們彼此說出的那些話。」
我們彼此說出的那些話。那些傷人的話。
我的腦海中倏然飄出他用抑鬱口吻說出的那句話──『我可能不夠喜歡妳……』
「然後呢?」我低語問道。
「我發現,其實我真的不夠珍惜妳,對我來說,妳的存在總是過於理所當然,我甚至很難去把沒有妳的歲月單獨抽離出來。我很對不起妳。」
語畢,他伸手碰觸了我的左臉,抹去了我臉上的淚水。
此時我才發現原來我哭了。即便我並不想哭的。
「凱璇,妳還愛我嗎?」他突然這麼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