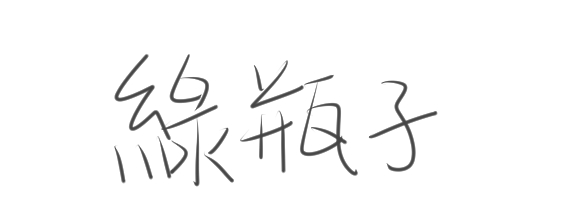我完全不知道我是怎樣醒來的,就在一個虛無的空間之中緩緩甦醒。擺設不像是我家,也不像是任何一個我所熟識的位置,我就這樣躺在軟到讓我脊椎疼痛的鵝黃色系床鋪上,我拉了拉床擺,發現有個物體卡在我的腳踝邊,壓住了棉被。
是個亮紅色的大紙盒。太顯眼了,讓我一時無法會意過來。
我端詳了四周,是間頗大的房間,床邊的矮櫃放著一只銀白色電話還有浪漫的檯燈,還有一個精緻漂亮的玻璃寬杯,裡面裝著透明純淨的水。
輕輕將盒子撈了過來(真的是用撈的姿勢),我發現我真的全身痠痛,但是卻衣衫完整。我似乎可以相信我並沒有因為喝酒而跟任何人發生不該有的親密關係,但是怎麼來到這裡的我卻無法連貫而起。
盒子上方有張卡片,是很舒服的青蘋果綠,我打開之後卻發現上面沒有任何的字跡。就像自己被玩弄了一樣。
紅舞鞋女孩
-
-
就像是她家的廚房一樣,舞鞋女孩非常熟悉的走到了吧檯前坐下,然後對著酒保綻出一抹燦笑。
「帶朋友來?」酒保一邊擦著紅酒杯一邊問著。他長得挺為粗獷,雖留著豪氣的鬍子,整體卻非常的乾淨清爽。
「對啊,他可是我的老朋友呢!」舞鞋女孩回應著,轉頭看向我,「坐啊!」她拍了拍身邊的那張椅子。
這樣的她讓我覺得很陌生,不單單只是外表上的改變,連態度跟反應都很不同了。這樣的她已經不再特別,反而太融入了社會,成為了我身邊的任何一個女孩。那樣的笑容,那樣的談吐,那樣的服裝……就連喝酒的樣子都已經展現出她跟我之間的距離。
太遙遠了。
但是,我突然反問了自己:我曾經了解過眼前的這位女孩嗎?有過嗎?
這個答案很簡單,但我卻什麼話也回答不出來。 -
我沒有想到自己有那麼一天會去經歷別人被羞辱的狀況之中,也不知道該如何去處理這樣的狀況。陽光很刺眼的照射在她的身上,讓她的一席洋裝更加的閃耀。她哭了嗎?她崩潰了嗎?她很難過嗎?她需要人陪嗎?需要人安慰嗎?好多的問號浮現在我的耳旁,可是我卻無法向前邁向一步。
她轉過身來,我沒有看見任何的淚水掛在她的臉頰上,但是卻鑲上了一雙失神的眸子。
她看見我了,我很肯定。可是她卻選擇當作沒有看見,就這樣從我身邊緩緩走過,步調沒有任何的變動。 -
但是我看見了,在舞鞋女孩羞著一張臉跑去廁所假裝要補妝的時候,木匠男孩望了望水果盤下方的紙條,然後連看也沒看的直接揉成一小團丟到他喝完的杯子裡,當作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
我非常的震驚,然而卻不敢告訴那個擁有少女期待笑靨的舞鞋女孩。就這樣看著她猶如起舞一般,不停在木匠男孩邊旋繞著,那樣的愛慕,卻又刻意想要保持距離。我在婚禮結束之後跟學伴說到這件事情,但她卻沒有什麼太大的表情跟反應,只是輕輕的搖了搖頭,然後把新娘盤髮上的小紙片輕輕甩落。 -
舞鞋女孩是個非常相信宿命論的人,她深信自己跟海倫擁有同一份靈魂:叛逆不遵循世道規則。不過也因如此,她更相信自己最後一定也會因為如此而遭到悲慘的下場,就跟海倫不停的跳舞最後被木匠砍掉雙腳一樣。
「但是她後來上了天堂,天使帶她去的。」她對我說這句話的時候眼睛在發光。 -
因為種種巧合,我認識了這位紅鞋女孩,就像是既定的緣分。我和學伴成了一對,但是最難以想像的是後來這麼嚴謹的學伴和紅鞋女孩竟成了好朋友,她們經常挽著手一同散步行走,學伴總是穿著襯衫跟牛仔褲,拎著那萬年不換的咖啡色側背包,而紅鞋女孩總是穿著一件比一件更華麗的蕾絲衣裳,但不可否認真的每件都很漂亮,她的頭髮不是維持一貫的捲度,就是梳上一個髻,把頭髮挽起來,格外典雅。但是我始終都沒辦法將視線離開那雙搶眼的紅舞鞋上,就像是她烙上的一塊標記。她走路就像在起舞,雖然我知道她只是在行走,但是卻有種莫名的輕快節奏,讓她的舞鞋在水泥路裡也像是在舞台上一樣輕盈。
-
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是在大學的迎新舞會裡。我雖然不是第一次看見穿著誇張的女孩,但是這樣的打扮還是讓我不禁想多看兩眼。
她穿著一件很古典的澎裙,繡著蕾絲的公主袖口,一層一層疊上去的細緻裙襬,領口相當精緻的把她的脖子給纏住了,整體的顏色相當灰黑色調,配上她微捲的長髮,感覺根本就不像是這個時代應該擁有的人。但是當她抬起頭時,便可看見她的一雙鳳眼嵌在有點削瘦的瓜子臉上頭,鼻子有些扁塌,嘴唇即使塗上了鑽石光芒的粉紅唇膏,還是難以將它變厚。 -
在愛情裡,如果真的有那麼一雙紅舞鞋,讓人可以無法停止的在其之中跳出生命之舞,那麼是不是誰都可以擁有勇敢的力量呢?
可惜最終,我們沒有一個人是海倫。
沒有得到舞鞋的力量,也沒有勇氣掙脫它。